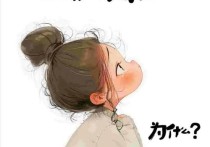梅雨记
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江南的梅雨,总是这般不疾不徐地来,又悄无声息地去。人们还未察觉,空气里已然渗出了湿意,先是若有若无,继而浓重得能拧出水来。
起初是雨丝,细如牛毛,斜斜地织在空中。瓦檐上渐渐聚了水珠,一滴,两滴,断断续续地敲在石阶上。卖豆腐的老王依旧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只是竹扁担上多了一块油布,盖着雪白的豆腐。他的布鞋踩在青石板上,发出"噗噗"的声响,像是踩在了吸饱水的海绵上。
巷口的阿婆把竹椅搬到了屋檐下,手里择着苋菜。菜叶上的水珠滚来滚去,终于"嗒"地一声落进搪瓷盆里。她时不时抬头望望天,嘴里嘟囔着"晒不干衣裳"之类的话。隔壁张家的媳妇正忙着把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往屋里收,手指一摸,布料还是潮乎乎的。
河边的石板路生了青苔,走上去要格外小心。摆渡的船夫老李蹲在船头抽旱烟,烟锅里的火明明灭灭。河水涨了,漫过了几级台阶,浑浊的水面漂着几片榕树叶,打着旋儿往下游去。
杂货铺的刘掌柜最烦这天气,盐罐子返潮,火柴也划不着。他拿着块干布,不停地擦拭玻璃柜台,可转眼又蒙上一层水雾。倒是卖伞的赵家生意兴隆,油纸伞、洋布伞,一字排开在店门口,淋了雨反而显得油亮亮的。
小学校的教室里,黑板上的粉笔字总是很快就模糊了。孩子们的手指在课桌下悄悄画着"驱晴娘",盼着老天爷开眼。可梅雨不管这些,依然不紧不慢地下着,有时一连十几日不见太阳。
只有茶馆里的说书先生照例拍响了惊堂木。"这雨啊,"他呷了口茶,"下得正是时候。"底下的茶客们便都静下来,听他讲那白娘子水漫金山的故事。窗外的雨声淅沥,倒像是给这传说配了乐。
梅雨终会停的。当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,人们才发现,墙角不知何时已爬满了蜗牛,拖着银亮的涎线,慢吞吞地向阴处挪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