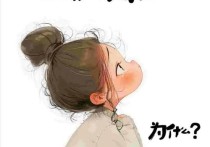他乡的腊味
年关将近,巷口那家湖南腊味铺的生意又红火起来。每日清晨,铺子前便排起长队,多是些异乡人,操着各处方言,伸长脖子候着那一挂挂油亮的腊肉。
店主姓陈,五十来岁,紫膛脸上刻着皱纹,像极了腊肉皮上的褶子。他操刀的手极稳,薄薄一片腊肉能照见人影,却总被顾客抱怨切得太瘦。"现在的人哪,"老陈常摇头,"连肥肉都不敢吃了,还尝什么腊味?"
斜对门的张老师是常客。他总在傍晚来,拣那最肥的腊肠,说是要炖萝卜。"湖南人吃腊味,讲究的是肥瘦相间。"他推推眼镜,掏出手帕擦汗,"我娘做的腊肉,肥膘有三指厚,蒸熟了颤巍巍的,能香透三条巷子。"
腊八那天,铺子里来了个年轻人,要买全瘦的腊肉。老陈皱眉道:"后生家,腊肉没了肥油,跟嚼木头有什么两样?"年轻人支吾着说是医嘱。老陈叹口气,从柜底翻出块陈年火腿,削去表层油脂,仔细包好。
春节前一周,老陈突然歇业。听说是老家的母亲跌了一跤。再开张时,他往腊肉堆里添了几串通红的手工香肠。"我娘捎来的,"他搓着冻裂的手,"说城里买的缺了柴火气。"
元宵节后,巷子里的腊味香渐渐淡了。只有张老师家的阳台上,还挂着半截暗红色的腊鱼,在寒风里轻轻摇晃,像一尾搁浅的船。